钱声广先生的这篇《写写麻雀》,是一篇立意深远、情感真挚的散文。它从“小人物”麻雀入手,通过历史的钩沉、文学的映照与个人细腻的观察,完成了一次对平凡生命的重新发现与深情礼赞。
一、 立意:为“小人物”正名
文章开篇便坦诚了作者乃至一个时代对麻雀的“偏见”。这种偏见源于司马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经典论断,也源于其貌不扬、不善表现的外在。作者将麻雀定位为鸟类世界里的“平民阶层”,这一定位本身就带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他欲为之“写写”的冲动,正是一种为被忽视、被误解的“小人物”书写历史、表达心声的自觉。
文章最触目惊心之处,在于对那段“人雀大战”历史的平静叙述。“两年时间共消灭麻雀16亿只”,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源于人类傲慢与无知的巨大悲剧。作者在此并未过多宣泄情绪,而是以“万幸”一词转折,引出了麻雀身份的戏剧性转变——从“四害”之一到“三有”动物。这一对比,强烈地批判了人类基于自身利益对自然生命的粗暴评判,也凸显了科学认知与悲悯情怀的重要性。
二、 叙事:温情与诗意的交织
在宏大的历史悲剧背景下,作者巧妙地插入了一个“老太太与麻雀”的温情故事。这个片段如同一束暖光,照亮了那段灰暗的岁月。老太太的善良与麻雀的信任,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图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生命平等的真谛。这一细节不仅丰富了文章的情感层次,更以个体的微光对抗了时代的荒谬,彰显了人性中不变的良善。
紧接着,作者将笔触探向文学传统,为麻雀寻找文化上的知音。他引用了现代诗人谢延龙的《七律·咏麻雀》,诗中“不乞娇浮成候鸟,甘求坦荡灭心机”的评价,将麻雀提升为一种不慕虚荣、心性坦荡的精神象征。而更为精妙的是对苏轼《南乡子》的解读,在苏轼笔下,寒雀不再是俗物,而是早春的使者、梅花的知音,它们“争抱寒柯看玉蕤”,充满了爱美之心与生活情趣。这两处引用,一今一古,从道德与审美两个层面,彻底为麻雀“平反”,使其形象从“目光短浅”跃升为“自在乐春秋”的智者。
三、 观察:生存智慧与时代变迁
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书斋,而是深入到田野现实。他对麻雀筑巢过程的观察,细致入微。麻雀对筑巢地的反复勘察与选择,被作者形容为“调研”,充满了拟人化的理解与尊重。他引用托尔斯泰关于鸟类筑巢的论述,将这一行为上升到“本能”与“学习”并存的生存哲学高度,赋予了麻雀筑巢以庄严的生命意义。
然而,作者的观察也带着一丝忧思。随着乡村的“荒凉”,老屋倾颓,麻雀赖以生存的屋檐也随之风雨飘摇。朋友那句“它们中的一部分也学着人类迁徙去了城市”的戏言,实则包含了深沉的感慨。乡村的变迁,不仅改变了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些“恋乡守土”的生灵的生存图景。当作者在城市的阳台上目睹麻雀群“开会”或“举行集体婚礼”时,这份景象已不仅仅是趣闻,更成为了一个时代变迁的隐喻,以及生命顽强适应能力的证明。
四、 结语:生命的完成式
文章的结尾,作者将“鸿鹄慕云霄”的宏大叙事与“碌碌践天道”的平凡坚守并置,并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后者的价值。“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生命完成式”,这句话是全文的文眼,升华了主题。它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应仅由志向的高低、外表的华美来决定,每一个在岁月长河中坚守平淡、努力生存的生命,都值得被书写、被尊重。
钱声广先生的这篇散文,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他写的是麻雀,关照的却是所有如麻雀般平凡而坚韧的生命,以及我们应如何以更谦卑、更宽厚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世界。这正是优秀散文的力量:它让我们在熟悉的事物中,重新发现被遗忘的真相与感动。(文/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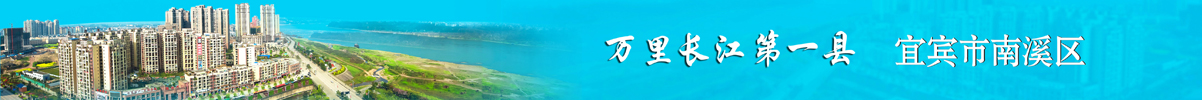

关注官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