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恼包村是在甲辰年的初秋时节。那天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参观时间,但留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感觉好像是到了江南某地,天蓝云白,空气清新,远山近水都是青绿色的。山水之间,怎么看都像是一幅画。
恼包村位于阴山山脉大青山南麓,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的一个村庄,是革命老区。恼包村的村名,源于蒙语“敖包”,意为“石头堆成的小山”,是蒙古族人用于祭祀的场所。当地村民笑称,当年因山西移民初来时发音不准,敖包逐渐被叫成了“恼包”,后来干脆将错就错,赋予它“烦恼抛却”的新寓意。
历史上的恼包村是个地势北高南低,频繁遭受洪水侵袭的荒凉贫瘠之地。 300多年前,山西的李姓家族率先迁居至此,垦荒谋生。随后又有诸多姓氏的家族相继迁入。他们与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人一道共建家园,形成了一个浓厚的山西传统风俗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村落。
走进恼包村,当年那种垦荒耕地的小村落,已化作了一座宜居小镇。村西是古朴典雅的传统院落,青砖碧瓦,雕梁画栋;村东则是欧式的现代楼宇,尖塔高耸,金碧辉煌。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晋味十足的民俗大集与超现实格调的恼包水世界比邻而居,颇有“迪士尼”韵味的游乐场与摩天轮南北呼应。这种中西合壁、古今交融的和谐景象,展现了恼包村独特的文化魅力。
我短时间与同行人员脱了一会“单”,驻足在美丽的天鹅湖边,欣赏着那只有在江南水乡才能看到的景致:水色潋滟,波光粼粼,轻舟荡漾。
不远处,湖心岛上有一对银发夫妇正在投喂锦鲤,鱼群跃起时,水面碎金闪烁,倒映着他们身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标语……这时,一只翠色的鸟儿飞了过来,落在旁边的柳树枝头,伸出嘴不停地梳理着羽毛,一会儿又掠过水面停在拱桥上四处张望。
我快速地追上了同行人员。到了村史馆,接待我们的村委会同志指着墙壁上那一幅幅珍贵的图片,向我们介绍恼包村人从当年的垦荒谋生到如今产业兴旺的传奇故事。其中有一张泛黄的照片让我注目良久——一位裹着头巾的妇女站在洪水中拄锹而立。陪同的同志解释说:这是1962年的李桂花奶奶,洪水曾三次冲垮过她的家,这是她帶着全村妇女在挖渠排水。后来,这段渠被叫作“桂花渠”,现在已在渠上修了玻璃栈道,成了一个景点。随行中有人无不激动地补了一句:游客们踩着的不仅是风景,更是老一辈的脊梁。
村委会的同志递给我们一杯用本地沙棘制成的茶,继续介绍道:2013年,乘着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东风,恼包村被列为呼和浩特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民集体决议通过“整村迁建”规划,保留了原有村落的文化肌理,同时引入现代化基础设施。在实际推进中,原本计划打造一个如江南水乡般宜居的青山水镇,有专家说这里缺水缺资源,搞旅游是异想天开。可我们偏把劣势变特色——没水就挖人工湖,没古迹就复原山西大院。谁知道抖音上一条“塞外小江南”的航拍视频,让恼包村火了!现在年轻人回来开民宿,老太太们蒸花馍成了网红伴手礼。他指着窗外排队打卡的游客,“乡村振兴啊,有时候就差一个敢想的念头。”
他告诉我们,恼包村从2013年启动迁建项目,到2024年上半年,已完成了多项住宅和商业设施,现已发展成为一个集生态宜居、特色旅游、民俗餐饮、生态养老、休闲商务、影视拍摄、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新型综合性特色的宜居小镇。截至2024年,村集体年收入从迁建前的不足50万元跃升至2000万元,游客量年均突破了百万人次。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火如荼的当今,恼包村把自己一个没有诗意的名字演绎成一个诗与远方的网红打卡地,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不可否认,这是乡村振兴进程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成功范例。
当我们行走在文化旅游产业园区,那修缮一新的明清时期留存下来的农家四合院,修旧如旧,保留着往日的容貌,不禁让人感叹;园内的文体活动中心、民俗大集以及游客休闲娱乐中心,同样让人流连忘返。在民俗大集的面塑坊里,山西传统花馍与蒙古族祭敖包用的奶食模具并排陈列。在文化大院里陈列的每一件实物,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它们是村民对先辈们艰难创业的感佩,更是维系村民身份认同,记住“根”和“魂”的载体。
于是,我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的一句话:“你可以把一个男孩从乡村的土地带走,但你却不能把乡村从男孩的身上带走。”是的,你可以把一个人从生他养他的恼包村带走,但你永远不可能把恼包村从他的心中带走。因为,他们的“根”已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魂”也紧紧地与家园系在一起。
家园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由传统文化、民风民俗、河流街道、声响气息等等共同构成的生存气场。恼包村这个镶嵌在敕勒川草原上的明珠,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无不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开阔与壮丽,他们抓住了人们的家园感,抓住了人们对过往不由自主却强烈的怀想。所谓的故土难移,所谓的乡愁,盖源于此。
离开恼包村时,我们在村口遇见一群写生的美院学生,他们画笔下的恼包村,是飞檐翘角衬着摩天轮的轮廓。我忽然明白,乡村振兴从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只要根脉不断,传统与未来本就可以同框。
作者简介:
钱声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县域经济学会特邀副会长,四川乡村文化艺术院执行院长,四川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原副主任(副馆长)、一级巡视员。著有杂文随笔集《官道拾遗》《仕途微言》《宦境闲语》和散文集《与山结缘》。
上一篇:沐川行
下一篇:已经是最后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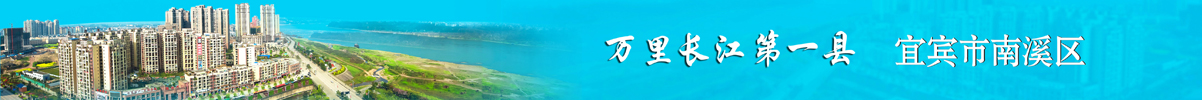

关注官网微信